【記者廖宥婷/台中報導】
我的任務就是去搭一座愛的橋梁,讓願意給予的人跟需要幫助的人,在愛裡相遇。
我在張秀菊基金會服務迄今已進入第九個年頭,這份工作其實是禱告來的。我從事過兒童教育,也曾在出版界服務,擔任志工十多年,但從來沒有想過,有一天會在社福機構工作。
因為這份工作,過去八年多,我見證了許多愛與感動的故事,原來社會上有不少人願意付出和給予,而我的任務就是去搭一座愛的橋梁,讓他們跟需要幫助的人,在愛裡相遇
持續的愛心好難
八年前,我和同學因緣際會來到張秀菊基金會參加志工活動,這個基金會是個特別的機構,兒少之家裡面的孩子大多是受虐的失家兒少,必須受到政府保護,他們的行蹤都不能對外曝光。
記得當時基金會執行長郭碧雲輕輕拉著我的手,對孩子們說:「以後美華姐姐來陪你們讀書好嗎?」
「好!」孩子們異口同聲說。
突然,有個孩子站起來,冒出一句台語:「你會來多久?」
我當場被戳了一下,剛開始心裡有點不舒服,但這也讓我感觸很深。我發現,這些孩子跟別人不同,他們生命中的大人總是來來去去,面對這些帶著善意而來的志工,有時好不容易培養出感情,沒多久又消失不見,「我才剛喜歡你,你怎麼就不來了?是不是我哪裡不夠好?」,就像再度被大人拋棄,感覺很受傷,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。
原本沒打算長期來陪讀,但衝著這句話,我用台語賭氣似的對那個孩子說:
「我會一直來,到你娶某生子!」
一次的愛心很簡單,但要持續真的很難。
許下承諾後,我發現要實現這個承諾很不簡單。我家住台中市北屯區,每次要到距離約二十公里遠的石岡區陪孩子讀書,下班時間開車過去,單趟車程就要四十五分鐘。覺得好遠、好累、想放棄的時候,我的腦海就會浮現那個當面吐槽的孩子,讓我更堅定要遵守自己的諾言。
能為孩子做什麼
我擔任陪讀媽媽有一、兩年的時間,這段時間,我的心深深地被這些孩子觸動了。看到兒少之家的孩子受到家境的影響,難免耽誤到課業學習,有的到了國中還不會數學的除法,那時我兒子已經是高中生,課業成績表現不錯(後來考上台大),我說服兒子跟我一起去擔任課輔志工,搶救弟弟們最弱的數學。
機構裡的孩子每個人都有一段充滿無奈的故事,他們別無選擇的被迫提早面對生命中不完美的一面。當初那個質疑我能否持續來陪讀的孩子,很小就被送到兒少之家安置。他曾經對我說:「你知道我是怎麼來的嗎?因為我媽有外遇,我爸就殺了我媽……」說話的語氣輕描淡寫,不帶任何情緒,像是在講別人家的故事,早熟到讓人心疼。
我主要負責陪讀的孩子,其中一個叫小楷(化名),就讀國中,他沒有爸爸,媽媽精神異常,只要喝酒就會傷害小孩,甚至會拿酒瓶砸孩子的頭,這讓小楷對母親的角色充滿敵意。只要我關心他功課寫完沒,立刻就像全身長滿尖刺,變得非常不友善,甚至口出穢言,但他又喜歡盯著我看,常找機會在我身邊出沒,渴望得到關注。
另一個陪讀的孩子小華(化名),就讀國小五年級,個子瘦小的他像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裡,無論問他什麼,答案都是千篇一律的「不知道」,連聯絡簿、作業本在哪裡也都不知道。我鼓勵孩子拿書來看,發現這個孩子看書的速度很快,沒兩三下就翻完了,原來他不認識字,連注音也不會,只好挑有圖畫的地方看。我特地挑選繪本童書,帶著他一個字、一個字學習。
有次,小華把書翻到一半就停下不念了,繪本正好停留在「一隻小白兔跑到山上看到皎潔月光」的畫面。我問小華發生了什麼事?
「那天,爸爸把我載到山上,就丟下我跑掉了,我很害怕,就一直跑、一直跑……」孩子想到小時候,在一個月圓的夜晚被父親遺棄在山林裡的恐怖回憶,終於把梗在心底的話說出來,那次是我第一次聽到小華說這麼多話。
需要的是同理,而不是同情
來到機構的孩子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。有些孩子受到的苦難特別多,從小他眼中的爸爸媽媽都是這樣對待孩子,他以為這樣的對待是正確的,這些苦難也是正常的,等他警覺到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時,他已經遍體鱗傷。
我常跟我的兒女開玩笑說:「媽媽的手臂好粗喔,因為我都沒有打小孩鍛鍊身體!」我的孩子從來沒有被父母打過,無法體會被大人揍的痛苦。
有些人生命中帶的苦比較多,有些人生命中帶的甜比較多,吃甜的人很難去想像吃苦的人口中的那種滋味,很難去體會他們過的是怎樣的生活,外人只能聽、只能看,無法感覺。我真的很希望這個社會不要對弱勢者視而不見,但是他們需要的不是我們的同情,而是我們能不能同理他,同情和同理是不一樣的。同理是要站在對方的立場,去體會他的感受,傾聽他說的話,更重要的是理解與接納。
張秀菊基金會是孩子愛的庇護所,能讓這些命中帶苦的孩子,過著三餐溫飽、正常學習的生活,同時養成正確的品格和價值觀,在十八歲獨立之前,鍛鍊好強健的體能和一技之長,不因原生家庭的不幸導致想不開或混幫派。
我是兩個孩子的媽,現在我要當一群孩子的媽。我們要成為孩子們生命中的逗點,而不是句點,等孩子長大,就能不斷去創造他們生命中的驚歎號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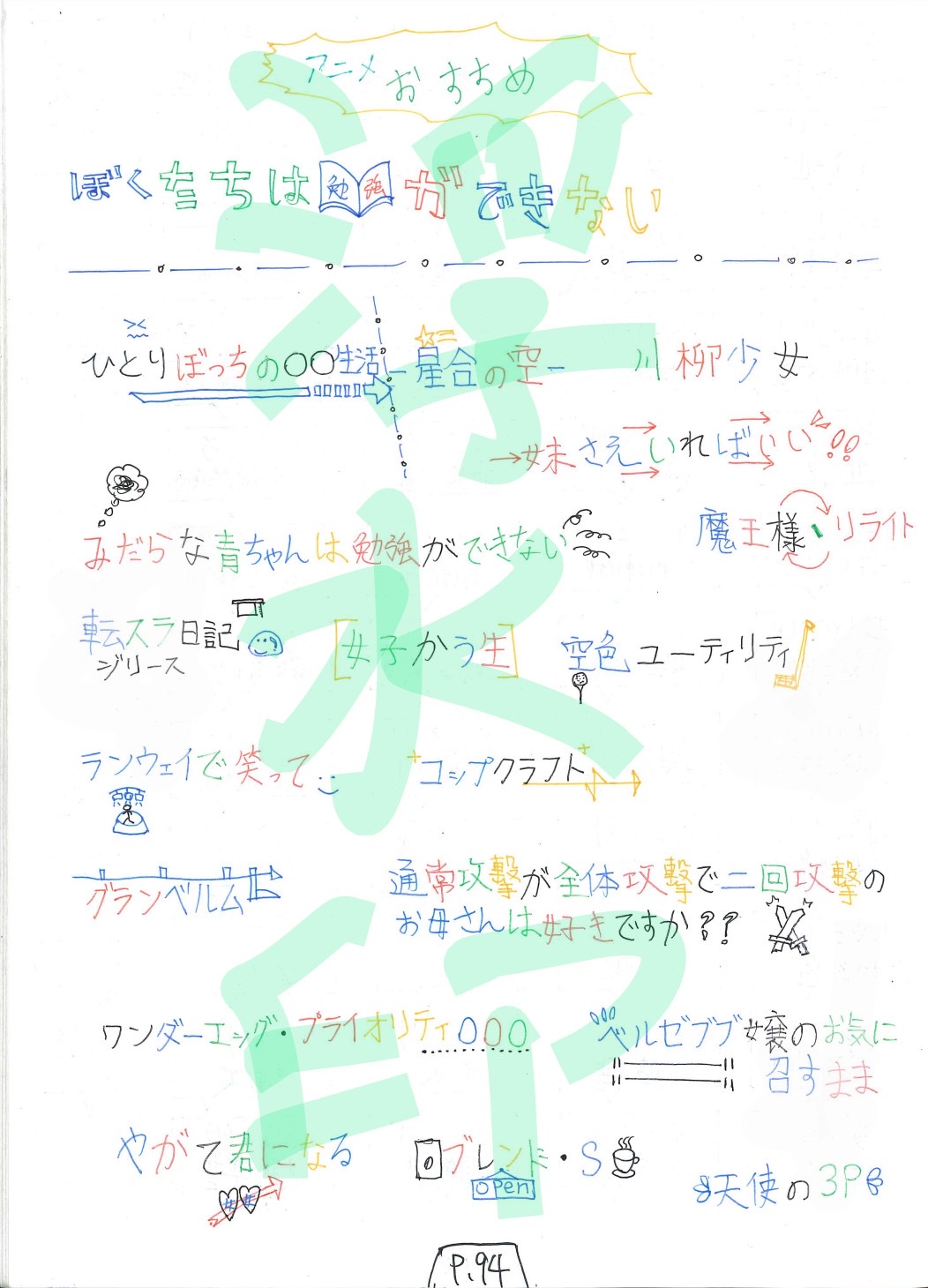
![第七屆國家環境教育獎[屏東縣]蔡正男、六堆客家園區獲特優 民和國小、里德社區獲優等@電傳媒](https://2udn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0/09/09241600952974_af2.jpg)
